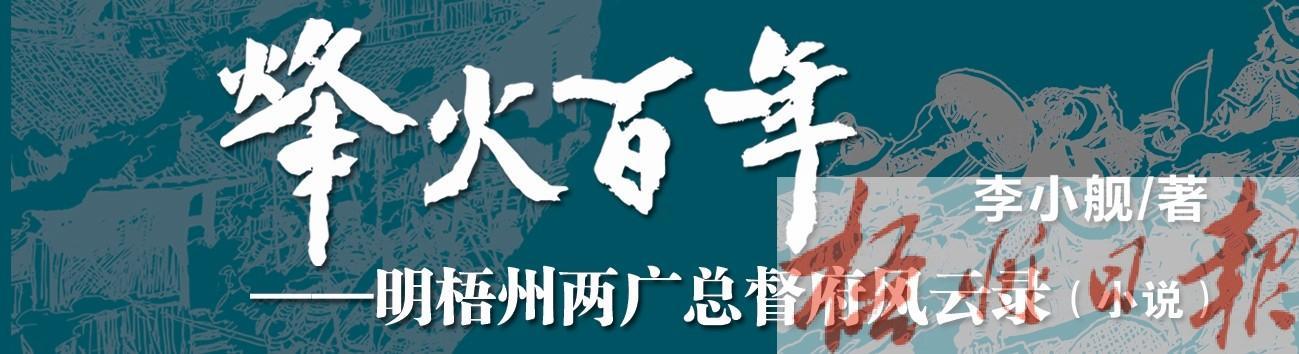为了更好地控制广东,韩雍又在广东省会广州和西江中游的肇庆两个府城建起了规模宏大的总督行台,以便日常到广东各处巡视往来。
广东省会广州的总督行台在府城西。该行台建有正堂五楹,穿廊一楹,后堂一楹,左右耳房各三楹,堂东为运筹堂,西为喜雨堂,东西厢房各三楹,仪门、大门各三楹,门外赏功所,前后六楹,左右官厅各三楹,南为官房,前后六楹。
肇庆的总督行台在府城东。该行台正堂五楹,穿廊一楹,后堂五楹,左右各为耳房,堂西衙二层,层各五楹,堂后为广益堂,五楹,东西穿廊各七,后曰读书楼,堂东曰大观楼,楼五楹,仪门、大门各三楹,门外左为坐营司、赏功所,右为中军厅、医药局。经过如此一番经略布局,韩雍坐镇梧州,便真的有一种“总制两广,扬威百粤”的感觉了。
此时的韩雍手握重权,兵饷充足,皇上宠信,总镇太监陈瑄与总兵官陈锐都对他相让几分。每当韩雍出入总督府,都要擂起府衙中所列的几十面铜鼓以为仪仗,左右随侍指使的都是三品官员,威风八面,尊严有如王公。凡有公事,两广布政使司与按察使司两司正使及以下官员,皆到梧州总督府参谒交代,均不敢以地方大员自居。三品以下官员,到了总督府, 先于门外等候,有如小吏,待韩雍接见时,则长跪禀事,战战兢兢。两广官员谒见总督行跪礼,是由韩雍的威势所使,此后很长时间都不能纠正过来。按先朝之制,只有总兵官列营,才使用举炮奏鼓吹的仪式。韩雍以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开府梧州,凡列营升帐都用此仪式。自韩雍开了头,从此以后,三边、宣大的总督以至内地带提督的官员都使用此种仪式了。在军营中,副将、参将以下,凡参见韩雍,都盔甲整齐,不敢轻率随意。广西与广东的镇守宦官,向来自恃来自皇帝内宫,都十分骄横,此时慑于韩雍之威,也只好收敛起来,不敢放肆。
如此一来,两广从军中到地方,做到了号令统一,令行禁止。那些心中不忿的地方大员与镇守宦官,敢怒而不敢言,只能等待韩雍倒霉之时。
韩雍在两广虽盛极一时,显得踌躇满志,但毕竟远在蛮荒的岭南,连年征剿,终日奔波,劳心劳力,又加上南方的瘴气暑热,不时会有心衰力竭、疾病缠身之感。韩雍有两首诗写出了自己的这种状况。
辛卯岁年五十须鬓有变白者
百粤平来见二毛,七年犹未脱征袍。
圣明倚托非常重,敢对时人话独劳?
忧劳万状与谁论,一点丹心祗自扪。
白尽鬓毛何足惜,只惭衰朽未酬恩。
韩雍的另一首诗中又说到了自己患上头痛的疾病。
谢陈总兵送氈帽
瘴乡风力恶,头骨痛难禁。
新帽劳君送,高情爱我深。
清晨笼短发,暖气温华簮。
感德惭无报,缄诗表寸忱。
韩雍自从任职两广,连年征剿战伐,终日板着面孔,杀气腾腾,难免心躁气粗。因此,公务之余,韩雍经常邀些同僚好友,文人雅士,游山玩水,饮宴欢娱,诗书酬唱,以此调适心情。在总督府休憩处的友清堂,原来植有古松三十株,韩雍叫人移来古梅十五株、修竹三百竿,环植于周围,号之“友清书院”。兴之所致,便写了一篇《友清书院记》,既寄情于物,又表明心迹。
两广总兵官陈锐在友清书院看到此文后,便请韩雍为总兵府中的双秀轩题诗,韩雍随即为他题了一首诗。
两广总镇太监陈瑄知道后,请韩雍为自己在总镇府中号“静庵”的住处也写一篇文记,以便留传后世。韩雍又欣然命笔,为他写了一篇《静庵记》。自号“竹坡”的广西总兵官欧信,也赶紧求韩雍为自己写了一篇《竹坡记》。于是,两广众官便纷纷求韩雍题写诗文,甚至连镇守广东市舶司的杜太监病逝,也请韩雍写祭文。
韩雍乃是进士出身,自然是雅好赋诗作文。平日看他似豪气冲天,威风八面,其实长年离乡别井,在远离繁华京师的岭南蛮荒之地为官,不免会生出一种孤寂感,生出许多乡情乡愁、人生易老、英雄迟暮的感觉来。特别是遇有来宾归客,或官员进京、升迁、致仕回乡,或离开这蛮荒之地,都会生出一番感慨。于是无论职衔高低,韩雍都慷慨宴请,赏赐馈赠,题诗寄语,以表难舍之情。
一天,在梧州府城外商市五坊路的一家立着“广西贡品上品精品布料一应俱全”通天招牌的布庄里,梧州府衙的师爷正在采购布匹:“瑶斑布两匹、彩锦两匹、葛布五匹……”(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