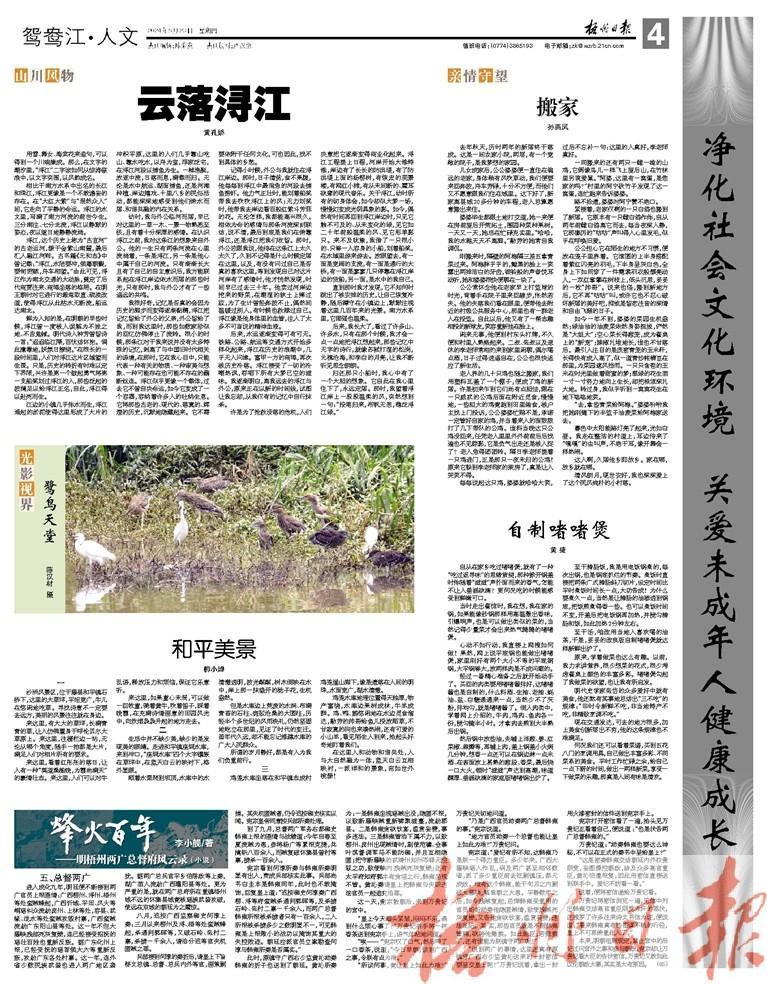去年秋天,历时两年的新居终于落成。这是一间农家小院,两层,有一个宽敞的院子,是我梦想的家园。
儿女成家后,公公婆婆便一直住在偏远的老家,身体稍有风吹草动,我们便要来回奔波,舟车劳碌,十分不方便,而他们又不愿意跟我们住在城里。这下好了,新家离县城20多分钟的车程,老人总算愿意搬出来住。
婆婆毕生都跟土地打交道,她一来便在房前屋后开荒拓土,围园种菜种果树。一天又一天,她活在忙碌充实里。“哈哈,我的水鞋天天不离脚。”勤劳的她常自我调侃。
刚搬来时,隔壁的阿梅隔三差五拿青菜过来。阿梅胖乎乎的,黝黑的脸上一笑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银铃般的声音悦耳动听,她和婆婆很快便聊在一块了。
公公常怀念他在老家早上打篮球的时光,背着手在院子里来回踱步,怅然若失。他的失落我们看在眼里,便带他去附近的村级公共服务中心,那里也有一群老人在投篮。自此以后,他又有了一帮志趣相投的新球友,笑容重新挂在脸上。
闲来无事,他便到村东头打牌,不久便和村里人熟络起来。二叔、张叔以及退休的李老师常相约来到家里闲聊,偶尔喝点酒,日子过得逍遥自在,公公也很快适应了新生活。
老人养的几十只鸡也随之搬家,我们用塑料瓦盖了一个棚子,便成了鸡的新居。许是初来乍到它们尚有点胆怯,跟在一只威武的公鸡后面在附近觅食,慢慢地,一些胆大的鸡竟跑到田里偷食,被户主找上门投诉,公公婆婆忙赔不是,承诺一定管好自家的鸡,并当着来人的面狠狠打了几下带队的公鸡。谁料当晚这只公鸡没回来,任凭老人里里外外前前后后找遍也不见踪影,它是负气出走还是被人捉了?老人急得团团转。隔日李老师提着一只鸡进门,正是那只一夜未归的公鸡!原来它躲到李老师家的柴房了,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每每说起这只鸡,婆婆就哈哈大笑,过后不忘补一句:这里的人真好,李老师真好。
一同搬来的还有两只一雌一雄的山鸡,它俩像鸟儿一样飞上屋后山,在竹林里另筑爱巢。“阿婆,这里有一窝蛋,是您家的吗?”村里的阿宁砍竹子发现了这一窝蛋,连忙跑来告诉婆婆。
路不拾遗,婆婆对阿宁赞不绝口。
紧接着,老家仅剩的一只白鸽也搬到了新居。它原本有一只雌白鸽作伴,自从两年前雌白鸽离它而去,每当夜深人静,它那凄厉的“咕咕”声叫得人心里发毛,似乎在呼唤旧爱。
公公担心它在陌生的地方不习惯,便放在笼子里养着。它滚圆的上半身搭配着紫红闪亮的羽毛,下半身呈灰白色,全身上下如同穿了一件霓裳羽衣般漂亮动人,一双红掌攀在树枝上,低头沉思,妥妥的一枚“帅哥”。说来也怪,搬到新地方后,它不再“咕咕”叫,或许它也不忍心破坏新居的美好吧,抑或是留恋往昔的深情和自由飞翔的日子。
如今一年不到,婆婆的菜园生机盎然;绿油油的油麦菜依然身姿挺拔,俨然是“大姐大”;空心菜长得葱茏,成为餐桌上的“新宠”;辣椒扎堆地长,谁也不甘落后。最引人注目的是茂密青茏的玉米秆,长得快有成人高了,似一道青纱帐横亘在那里,为菜园遮风挡雨。一只只含苞的玉米在时光里做着甜蜜的梦;翠绿的花生苗一寸一寸努力地向上生长,却把根须深扎大地。转过身,我似乎听到一窝窝花生在地下咯咯地笑。
“去,拿些青菜给阿梅。”婆婆吩咐我把她刚摘下的半篮子油麦菜给阿梅家送去。
暮色中太阳能路灯亮了起来,光如白昼。我走在整洁的村道上,耳边传来了“嘎嘎”的虫叫声,不绝于耳,像开舞会一样热闹。
这人啊,久居他乡即故乡。家在哪,故乡就在哪。
清风朗月,现世安好,我也深深爱上了这个民风纯朴的小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