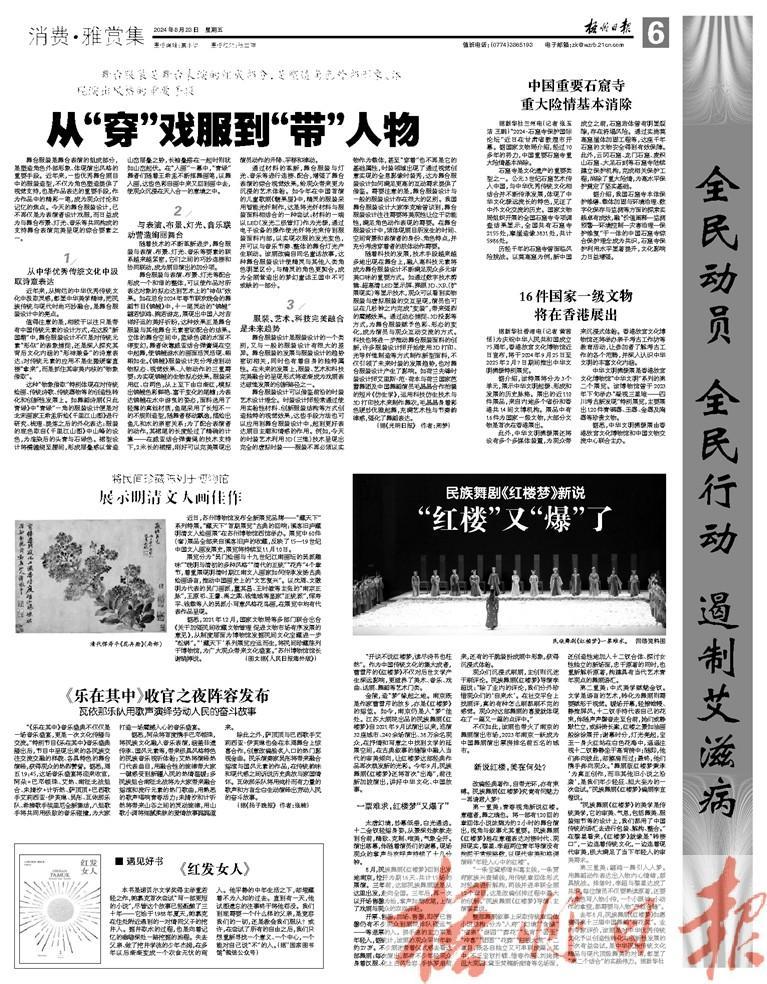“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曹雪芹的《红楼梦》不仅对后世文学产生深远影响,更滋养了美术、音乐、戏曲、话剧、舞蹈等艺术门类。
金陵,造“梦”缘起之地。南京既是作家曹雪芹的故乡,亦是《红楼梦》的摇篮。如今,南京仍是入“梦”佳处。江苏大剧院出品的民族舞剧《红楼梦》自2021年9月试演出以来,巡演32座城市、240余场演出、38万余名观众,在抒情和写意之中找到文学的延展空间,在古典叙事的缝隙中融入当代的审美倾向,让红楼梦这部经典作品再次焕发新的光彩。今年9月,民族舞剧《红楼梦》还将首次“出海”,前往新加坡演出,讲好中华文化、中国故事。
一票难求,红楼梦“又爆了”
太虚幻境,纱幕低垂,白光通透。十二金钗轻摇身姿,从景深处款款走到台前,精致、克制、唯美,气象全开。演出落幕,伴随着演员们的谢幕,现场观众的掌声与欢呼声持续了十几分钟。
8月,民族舞剧《红楼梦》回到出发地南京,拉开为期16天、共计15场的展演。三年前,这部民族舞剧就是从这里出发,走向全国。三年后,再一次以开场售罄为始,掌声如潮收尾,上演了戏剧与观众的双向奔赴。
开票、售罄,加场、售罄,即便已售罄仍有不少观众到剧院排队碰运气——等退票的人。拼手速的主力军是年轻人,据统计,该剧的观众平均年龄约27岁。不少剧迷带着仪式感去看这部舞剧:每次演出,都有不少年轻观众身着汉服、化上古风妆容、手执罗扇前来,还有的干脆装扮成剧中形象,获得沉浸式体验。
观众们沉浸式刷剧,主创则沉迷于刷评论。民族舞剧《红楼梦》导演李超说:“除了业内的评论,我们分外珍惜观众们的‘自来水’。在社交平台上找剧评,真的有种怎么刷都刷不完的感觉。观众对这部舞剧的喜爱就体现在了一篇又一篇的点评中。”
不仅如此,该剧也带火了南京的舞剧演出市场,2023年南京一跃成为中国舞剧演出票房排名前五名的城市。
新说红楼,美在何处?
改编经典著作,自带光环,亦有束缚。民族舞剧《红楼梦》究竟有何魅力一再请君入梦?
第一重美:青春视角新说红楼。意蕴者,舞之魂也。将一部有120回的章回体小说浓缩为约2小时的舞台演出,视角与叙事尤其重要。民族舞剧《红楼梦》胜在意蕴表达对接时代、观照现实,黎星、李超两位青年导演没有拘泥于常规路数,以现代审美和格调演绎“年轻人心中的红楼”。
“一条宝黛感情纠葛主线,一条贾府家族兴衰辅线,用传统章回体形式对经典进行解构,两线并进串联全剧12个章目,这是改编创排过程中最大的创新。”民族舞剧《红楼梦》导演、主演黎星说。
整部舞剧叙事上采取传统章回体小说结构,分为“入府”“幻境”“含酸”“省亲”“游园”“葬花”“元宵”“丢玉”“冲喜”“团圆”“花葬”“归彼大荒”十二章目,既各自独立又可串联成篇。其中,不乏宝钗扑蝶、惜春作画、刘姥姥逛大观园、黛玉焚稿断痴情等名场面,还创造性地加入十二钗合体、探讨女性独立的新场面,忠于原著的同时,也重新解析原著,构建具有当代艺术青年观点的舞剧语汇。
第二重美:中式美学赋魅金钗。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转化为舞剧则需要赋形于视觉。暖场开幕,轻撩帷幔、静推屏风,十二钗手持代表自己的花束,伴随声声磬音走至台前,她们或静默伫立,或斜倚长案,红楼之景如油画般徐徐展开;谢幕时分,灯光亮起,宝玉一身火红站在白色花海中,遥遥注视十二钗静静坐于高背椅中;随即,他们奔向彼此,却擦肩而过;最终,他们携手奔向观众。“舞剧版红楼梦秉承‘为真正创作,而非其他旧小说之沿袭’,是我们年少轻狂、胆大妄为的一次尝试。”民族舞剧《红楼梦》编剧李宜橙说。
“民族舞剧《红楼梦》的美学是传统美学,它的审美、气息,包括舞美、服装细节等的设计上,我们都用了中国传统的语汇去进行包装、解构、整合。”在黎星看来,《红楼梦》就像是“转接口”,一边连着传统文化,一边连着现代审美,极大满足了当下年轻人的审美需求。
第三重美:翩鸿一舞引人入梦。用舞蹈动作表达出人物内心情绪,颇具挑战。排练时,李超与黎星达成了共识,每位演员不仅要熟读原著,还要为角色写人物小传,一个小眼神、小动作的拿捏,都需要与人物“严丝合缝”。
去年8月,民族舞剧《红楼梦》如愿摘得第十三届中国舞蹈“荷花奖”。业内专家评价,该剧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予以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一次有益尝试,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品与现代顶级舞美的对话,彰显了“第二个结合”的实践伟力。 据新华社